從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這一目的出發,運用歷史解釋和目的解釋的方法,對于那些突破基本社會道德底線的威脅、引誘、欺騙性取證手段,仍應將其納入“等”字的解釋范疇予以禁止。普陀刑事律師帶您了解一下有關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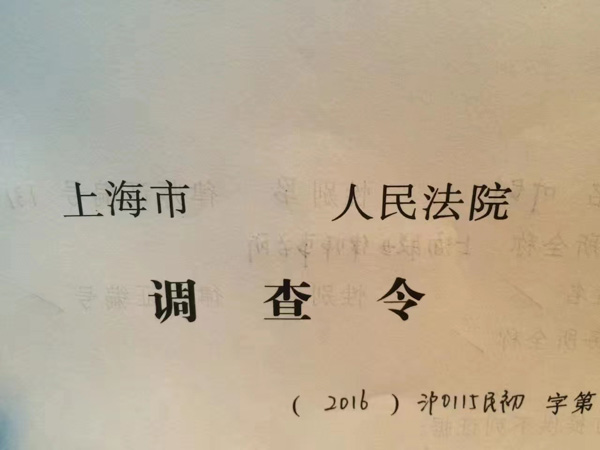
由此可見,從劃定規矩制訂原意上講,《消除非法證據劃定》第1條對“等”字的應用之所以不盡吻合漢語的用語習性,實乃逃避要挾、勾引、欺騙性取證的正當性問題而至。然則,暫不作出劃定,其實不意味著該類取證行動即同等合法。
比方,法律實踐中,偵察機關在偵辦職務犯法案件時每每以追查近親屬的法令義務為名對被追訴人舉行要挾,罕見審判用語如“你不說,就追究你老婆(丈夫)的刑事義務。咱們有證據注解,她(他)也介入你的犯法行動。”
這類以追查家人的刑事義務相威脅的審判體式格局,傷害了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家庭人倫,屬于打破基礎社會道德底線的要挾性取證,應屆法令阻止的非法手法取證,在法說明上應歸入“等”字所指領域。
在本案中,依據被告人章國錫的陳說,“7月22日下晝3點,他與被傳喚的老婆見了一壁后,他們說要將老婆當同案犯操縱,若不誠實交接就不放她……章國錫說,7月23日23時,他考慮到缺乏3歲的孩子需求賜顧幫襯,為爭奪寬大處理,就交代自己涉嫌受賄0、6萬元,還交代了和金恒監理公司的經濟問題,借用注冊監理工程師證書4年共獲得報酬3、6萬元。”
由此可見,本案中偵查人員以被告人不交代就要追究無辜近親屬刑事責任的方式對被告人實施了威脅,俗稱“親情逼供”。這種威脅性取證方式突破了社會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傷害了家庭人倫,極為不人道,司法上應作出否定性評價,將其納入“等”字所指非法方法之范疇予以禁止。

后面接頭的題目,實踐均可納入非法證據消除劃定規矩實體內容的領域,但要消除非法證據,立法層面除需要建立上述實體性標準外,還需要在程序上設置舉證責任分配、證明標準、證明程序等配套制度,以確保非法證據在審判中能被順利排除。
《消除非法證據劃定》第5條劃定:“被告人及其辯解人在休庭審理前或許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獲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告狀書之后,應該后行當庭考察。”由此確立了非法證據的后行考察準繩。
所謂后行考察準繩,是指法庭應該將被告方對于非法證據的抗辯列為優先事項舉行法庭考察,在此以前,案件實體部分應該停息考察。之所以實施后行考察準繩,是因為,一旦被告方的非法證據抗辯取得證實,非法證據被消除后,若無充沛證據證實被告人罪責,法官無須再進行案件實體部分的審理即可直接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以便及時終結訴訟,避免庭審無謂進行并減少訟累。
在本案中,一審法官不僅在法庭考察中嚴峻遵照了后行考察準繩,在被告方提出消除非法證據的請求并供應相干線索和證據后,隨馬上證據采集的合法性列為優先事項睜開法庭考察,并且在一審判決書中將訊斷明確分為“步伐部份”與“實體部份”分手舉行論證、說理,以致決心將“程序部分”放在“實體部分”之前進行論證、說理,以貫徹先行調查原則的要求。

普陀刑事律師認為,一審法院的這一做法,堪稱法院處理非法證據爭議的典范。尤其是其判決書的撰寫模式,更應該成為同類案件判決書的范本予以推廣。應當說,這一規定具有合理性,也有相關立法例可供參酌、借鑒。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3項即有類似規定:“被告陳述其自白系出于不正之方法者,應先于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